美味锅巴飘香来
文/时春华(辽宁北票)
小时候的我并不挑食,可在母亲做饭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她做干饭。每每母亲做干饭,只要我在家,总会屁颠屁颠跑前跑后,倒淘米水,抱柴禾,帮烧火。我这么给母亲打进步,一是我本来就听话懂事,二来呢,我有自己的小算盘,惦记着做熟干饭后留在锅底的那块大锅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比不得现在,不冒烟就能吃饭。那时候的农村家家做饭都用大铁锅,烧的是秸秆,使风助燃的是笨重的风匣。米饭在锅里煮到八分熟,母亲用笊篱在锅边上踅一下,捞起一点饭粒,饭粒破花没有生米芯算是刚刚好。母亲先是把米饭捞在一个铁盆里,待把米汤盛到另一个盆里,刷完锅,便把那盆刚刚捞出来的米饭扣到锅里。灶膛里撤了硬火,放些柴叶在灶膛或是把那些硬火余留的灰烬重新翻亮,把锅里的米饭焖熟至十分。我焦急地等待米饭出锅,不是我饿了,是我馋了,因为盛出米饭,总会在锅底有一张圆圆的、大大的、硬爽爽的锅巴。我真是服了母亲会掌握火候,因为锅里的饭要是柴填多了就会串烟,饭不好吃锅巴也糊了,柴少了锅巴就会发软,不筋道更不香。母亲绝对是个能掌握火候的高手,每次做干饭出来的锅巴,总是嘎嘣脆带着米香。这种做饭的方式相对来说费点柴禾,赶上冷天需要多烧柴就这么做米饭,要是不需要烧那么多火,母亲是烧开了水直接在锅里焖饭的,米锅烧开,饭到六分熟,母亲就用勺子撇了多余的饭汤,留下一点刚好能被灶里的柴烧靠下去,饭熟了,锅巴也成了。那时候我们常吃的就是小米饭、高粱米饭,小米的锅巴又香又脆,高粱米饭的锅巴比小米饭的锅巴厚,更有嚼头。干嚼,锅巴就咸菜疙瘩,或是抹上酱卷了菜吃,咋吃都吃不够。后来有了大米,做大米饭,我们还是照旧吃锅巴,只不过,跟小米高粱米的锅巴比起来,大米的锅巴有些硬,有时候吃着觉得垫牙。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居住在乡村的母亲做饭早就用上了电饭锅,即使在大铁锅里做饭,也多是蒸饭,因为母亲上了年岁,牙口不好,吃不得硬饭,更不敢再吃锅巴。那一日回家,和母亲聊起我们小时候吃的锅巴,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母亲笑了,她说,她有个新发明,做出来的锅巴香脆可口,老少皆宜。我便来了兴致,央求母亲给我们做。母亲并不着急,锅里烧开了水,用小碗舀上几碗玉米面,还抓了点白面掺上做黏合剂,母亲把混合了的面用开水烫成稀糊,把大铁锅掸干烧热,倒一些稀糊在锅底,用小木铲向四外摊开,摊完了,薄薄、黄黄的大锅巴也翘边了,第二张、第三张……母亲一气给我们摊了好几张。玉米面的锅巴又薄又香,我用小葱和芹菜叶卷了一大张,那滋味,比我小时候吃的锅巴要好上好多倍。回家后我也照母亲的方法,在饼铛里做过锅巴,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实际上,美味的东西不见得是贵的,粗粮细做在于花样翻新。美味锅巴飘香来,生活虽平淡,只要我们善于调剂,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精彩。
小链接时春华,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现就职于辽宁省北票市教育局信息中心。1992年毕业于朝阳市第一师范学校,选修音乐,酷爱文学,文风朴实接地气。热爱生活,热衷传播社会正能量。系朝阳市作家协会、辽海散文学会、北票市作家协会会员;《好名声网》特约助理编辑,此网站有《时春华好名声展馆》;《北票市报》特聘记者,此报刊有专栏《朝花夕拾》。在网络、刊物上发表作品60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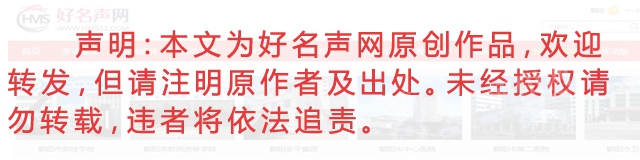
[编辑 直观 编审 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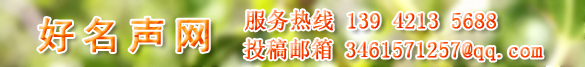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