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文图/谭廷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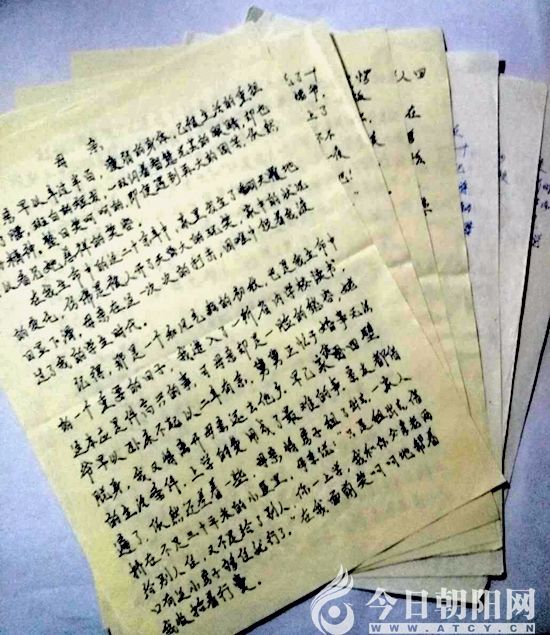
《母亲》手稿
母亲年过半百,头发斑驳,身体瘦弱,已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但她整日笑呵呵的,一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即便遇到再大的困苦,依然可以看见她慈善的笑容。
在我生命中的二十余年里,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是被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家道中落,每况日下,家徒四壁已不足过。母亲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为我的生活、学业昼夜不眠,为我撑起了一个完成而又幸福的家,陪着我度过了学生时代。
也许正是母亲的鼓励,那一年的初秋,我进入了省内的一所学校读书。这本应是高兴的事,可母亲的脸上却露出了愁容,姥爷卧病两年有余,舅舅正忙于婚事,无法脱身,而我又将离开她去他乡求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而且是那么远,那么久,她不放心啊。家徒四壁,上学的费用也成了她心中最大的烦心事。所有的亲友都借遍了,依然还差一些。母亲将房子租出去一半,一家人挤在不足三十平的小屋里。母亲说:“只是租出去,借给别人住的,又不是给人了,你一上学,家里就剩我和你爸,房子小点儿,够住就行了。”在我面前笑呵呵地帮着我收拾行囊。
起初,母亲说不去送我了,让我自己走。她说她需要照顾姥爷的,就不送我了,托了顺路朋友帮着照看。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看着她落泪。当我坐上远行的列车时,母亲还是来了,上了车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还是我去吧,不放心啊!”车走的是夜路,次日清早才到,这样白天就可以办入学手续。出于第一次离家的兴奋,在车上,我出奇地精神,拉着母亲唠这说那,母亲只是笑着,听着。夜深了,母亲说:“睡会吧!明个儿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呢,入学可是有很多手续要办,没精神可不行。”我应了一声回道:“妈,你也睡会儿。”她只是笑着点点头。
次日清早,下车时候,才发现母亲那双慈祥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她一夜未眠。
“你怎么不睡会儿?”
“我要是睡了,你的行李准备给小偷啊!”母亲笑呵呵地说。
在去学校的接送车上,母亲轻松地说:“去忙你的吧,其它的事交给我了。”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其实,入学手续很简单的,无外乎就是拿着报到证跑跑腿,填几张表格,录入些基本信息,然后就是分班,见见新同学,相互打个招呼,和老师还有辅导员见个面。当我回到宿舍时候,我呆住了,瘦小的母亲正蹲在两米多高的床铺上帮我铺着被褥。那床被褥是母亲前几天刚做的,连着毡子有十几斤重,她是怎么弄上去的?她看我发愣,笑着说:“愣着干嘛,不吃饭了?还不快去收拾一下。”我才注意到在床下的桌子上,放着我的生活用品,还有不少其它物件,满满的一桌子,好多都是新买来的,还贴着标签。刚才我办入学手续的时候看过了,这附近是不能买到这些东西的,也不知道母亲走了多少路。当我们收拾停当已是午后了,学校的食堂是可以点餐的,母亲点了个肉菜,看着我吃、陪着我吃,怕我饿着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她慈祥的脸上充满了对我的期望。“孩儿啊,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按时吃饭,在外面可不像在家里,多注意身体呀!有啥需要的你就打电话,在学校好好学习,别向你妈一样,没文化,单位一改制就没了工作,以后要有出息。家里你就不要担心了,有妈呢。给你安排好,我就放心了。”
母亲是下午五点的火车,当我把母亲送上月台,母亲说:“不行哭,男孩子哭啥,又不是见不着了。”说着,看着我笑了笑,转身向车门走去。望着母亲佝偻的背影,泪水在眼里打着转。不能哭,不要让母亲看见。她蹒跚着走过月台,先用手扶着门把手,用力向上提着身子,脚才小心地蹬在车门边上。她回头朝我笑了笑:“老了,不灵便了。”然后,就被后面的人催着挤着,像大海里的一艘小船。母亲在人群中被挤得左右摇晃着,好不容易挤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在车窗上我又看见她那慈祥的笑容,她只是想多看我几眼。这次分别不知多久才能再见,火车的汽笛声载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回家。
夜里,我安卧在母亲为我铺好的床铺上,此时的母亲还在车上,她又将是一个不眠夜啊!母亲这一送就是九百多公里,两天两夜的不眠不休。母亲啊,为了您的儿子,您做什么都是那么心甘情愿。
姥爷的病很重,在我到学校不久就去世了,在母亲的怀里走的,很安祥。母亲并没有告诉我,说怕我担心,这些都是舅舅后来和我说的。母亲早已过了天命之年,经历了三年痛失四位亲人的伤痛,就连最小的弟弟也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母亲在一次次的打击中病倒了,这一年我即将毕业,要去更远的地方工作。病床上的母亲嘱托父亲不要告诉我,让我安心学习,去寻找我的未来。放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母亲,我哭了,母亲却笑着安慰我说:“没事的,妈命大着呢,阎王爷不要我。”然后就看着我笑。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我有太多的顾虑,怕影响我今后的生活。我只是拉着妈妈那双粗糙的满是伤痕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流着眼泪。假期一过,我去了学校,母亲嘱托我:“好好干,知道你已经被大公司录用,我高兴着呢,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这一次,我没有听她的话,回到学校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今生最正确的决定,母亲陪我长大,我就要陪着她变老,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当我拿着毕业证和行李回家的时候,我挨了二十多年唯一的一次打,就算小的时候再调皮都没被母亲打过的我,这一天母亲真的动手了,打了我一巴掌。母亲哭了,哭得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流眼泪,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痛哭,最后默默地在床上抹眼睛。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知道母亲因为什么,但我不后悔这次的决定。我要陪着她走完她的下半生,我不会离开。父亲也在哭,父亲在恨自己没能力,在自责。我知道,母亲病倒以后,父亲也因急火攻心得了心梗,那一天我不在,是母亲的呼唤,救了父亲。
现在我毕业了,父亲和母亲都老了,那丝丝白发真的只是儿女债,历历深痕何只是岁月的痕迹?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我真的很难找到答案,也许有一天我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才会明白。
母亲永远都是笑着的,她用笑为我撑起一个家,她用笑战胜了病魔,她的笑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说:“人活着一天,就要快乐一天。笑是一天,哭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多笑笑呢!”现在我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逐渐转好,母亲坚强地用笑容默默地守护着我的家,也守护着那份属于她的幸福。

(本文原载于2018年05月12日今日朝阳网<文教><传统文化>栏目,转载时略有改动,原标题:《母亲》)
[责任编辑 寻冬]


 【好名声网】赶 考(时春华)
【好名声网】赶 考(时春华) 【好名声网】我的父亲(王文月)
【好名声网】我的父亲(王文月) 【好名声网】掐谷子(王铁兰)
【好名声网】掐谷子(王铁兰)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荤油拌饭(石玉梅)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荤油拌饭(石玉梅) 【好名声网】我的爷爷(王洪洋)
【好名声网】我的爷爷(王洪洋) 【好名声网】多情的香雪兰(王劲松)
【好名声网】多情的香雪兰(王劲松) 【好名声网】母亲的线笸箩(李兴坤)
【好名声网】母亲的线笸箩(李兴坤) 【好名声网】老叔的“小棉袄”(王洪洋)
【好名声网】老叔的“小棉袄”(王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