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门,那扇窗
文图/时春华(辽宁朝阳)
那个门,是我老家的大门;那扇窗,是我家对过三婶家的后窗。
我家的门洞以往是最热闹的,常驻者有我妈,前院三婶,再前院的二姐,我大嫂,后街的我三姨,过路停下来凑热闹或是偶尔过来的邻居也不少,大家在一起家长里短,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因为住得近,也因为投缘,我妈和我三婶交流最多。我妈和三婶没有秘密事,她俩都是敞亮人,从不对东邻西舍说长道短。我妈站在门洞里一嗓子就能把三婶招呼到后窗前,三婶也常常踩着小板凳敞开后窗招呼我妈,菜园里生菜能间着吃了,西葫芦下来了,从山上薅了点猪毛菜,从亲戚家拿来点稀罕玩意,这就是她俩交流的内容。还有就是我妈上山干活了,兴许回来晚了让三婶帮着喂喂猪,三婶出门了,晚上要是不回来让我妈帮着喂喂鸡鸭顺带着关上窗户,今天不回来就帮着填把柴烧烧炕。农村里无非就是这些活这些事。有时候都忙着,碰不着面,我妈在敞开的大门里看见了三婶家后窗的灯光或是三婶在后窗那听见了我妈回家咣啷大门的响动,都会嚷一嗓子,对个话,证明她们之间的惦记。我妈一遍又一遍看三婶家好几天不亮的后窗灯,三婶在后窗听,看我家总没开的门是常有的事。三婶家晚上灯也亮,我妈家的门天天也开,是她们回家和彼此相看的时间不同,所以就有很多错过,敲敲门,直到看见人才放心。
后来,我妈得了脑血栓,不能说话,呆在门洞里的时候,三婶,二姐,我三姨,我大嫂还是常来,只是发言的少了一个,我妈只能作为她们的倾听者,她心里有数,她常常望着三婶家的后窗叹息,因为她再也亮不出那嘹亮的一嗓子。
几年前,三婶去给儿子看孩子去了,走的时候我爸推着我妈去跟三婶告别,我妈恋恋不舍,三婶也是。大前年三叔意外去世,三婶就不回来了,二姐也去给儿子看孩子去了,我大嫂忙着养牛,三姨也有自己的活,门洞里常常就剩我爸我妈。
如今我妈去世了,门洞里空落落的。那个凉风习习的好地方,只剩下孤独的我爸。
我妈烧三七那天,三婶回来了,我们坐在门洞里,说起以往,说起我妈,泪眼婆娑,唏嘘感慨。真是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啊。
我家的门洞,地还是土的,爸爸老了,一个人住着不打算修了;三婶家的后窗,玻璃已经碎了好几块,一个铝篦子就当是一块玻璃放在那好几年了,三婶没有再回来的打算,现在她不想这房子的事了,这房子里有她和三叔的半辈子的记忆和回忆,孤零零一个人在这,睹物伤情,不好受。
我们回家关车门的响动惊动了老爸,看见我们,他眉宇间紧锁的愁苦才稍稍不见。我们跟他说,在进村转角的地方遇见了谁谁谁,老爸长叹一声,说:“唉,这营子啊,没剩多少老人了,这房子啊,慢慢儿就没人住了。”那语气里,让人生出一丝无奈和怜悯,就如我家空荡荡的门洞对着我三婶家空荡荡的后窗那般。
那个门,那扇窗,怎么就让我感觉我魂牵梦萦、千丝万缕的家,我的家乡,离我越来越远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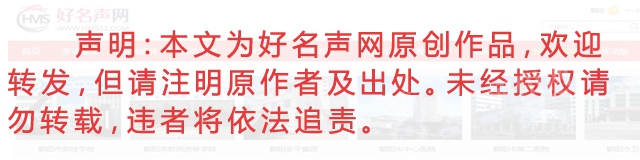
[编辑 熙楉 编审 春语]




 【好名声网】那个门,那扇窗(时春华)
【好名声网】那个门,那扇窗(时春华) 【好名声网】冰峪美景入画来(时春华)
【好名声网】冰峪美景入画来(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母爱情(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母爱情(时春华) 【好名声网】城市“氧吧”大凌河风景区(王洪洋)
【好名声网】城市“氧吧”大凌河风景区(王洪洋) 【好名声网】母亲缺席了端午节(时春华)
【好名声网】母亲缺席了端午节(时春华) 【好名声网】墙角的绿萝(王洪洋)
【好名声网】墙角的绿萝(王洪洋) 【好名声网】那条红色的拉毛围巾(时春华)
【好名声网】那条红色的拉毛围巾(时春华) 【好名声网】假领情结(时春华)
【好名声网】假领情结(时春华)